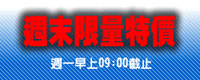|
許廣平講過一個關於魯迅的故事:「1931年,避難住在旅館的時候,有一位叫老楊的工友,當他是老教書先生,天天跟他圍爐子談天,叫他代寫家書,簡直不曉得他是魯迅,這就是十足的魯迅。」老楊大概沒讀過魯迅的書,所以「不識廬山真面目」;魯迅已矣,我們現在只能讀他留下來的書了。但是由此也未必能夠看到許廣平講的那個「十足的魯迅」。
周作人批評說:「我曾見過些魯迅的畫像,大都是嚴肅有餘而和藹不足。可能是魯迅的照相大多數由於攝影時的矜持,顯得緊張一點,第二點則是畫家不曾和他親近過,憑了他的文字的印象,得到的是戰鬥的氣氛為多,這也可以說是難怪的事。」又說:「魯迅寫文態度本是嚴肅,緊張,有時戲劇性的,所說不免有小說化之處,即是失實。」作者通過文字為自己塑造形象,並不一定要與日常生活中的本人完全一致;可是我們應該明白,這只是文字之中的作者而已,如果希望據此還原文字之外的他,那就需要小心一點。
且來舉個例子。周作人說:「在老家裡有一種習慣,草囤裡加棉花套,中間一把大錫壺,滿裝開水,另外一只茶缸,泡上濃茶汁,隨時可以倒取,摻和了喝,從早到晚沒有缺乏。」說來類似習慣好像並不限於紹興一地,我即曾見先父採用,稱為「茶母子」,盛在搪瓷杯裡,冬日放在爐台上加熱,兌開水喝。魯迅在東京時,也是這種喝法。「所用的茶葉大抵是中等的綠茶。好的玉露以上,粗的番茶,他都不用,中間的有十文目,二十目,三十目幾種,平常總是買的『二十目』,兩角錢有四兩吧,經他這吃法也就只夠一星期而已。」不過他後來喝茶就講究多了。許廣平說:「到了上海,改用小壺泡茶,但是稍久之後,茶的香氣會失去的,如果不是工作太忙,沒有時間細細品茶,他就會要求另換一壺。等到新鮮的茶來了,恰到好處的時候,他一面稱讚,一面就勸我也飲一杯。」然而魯迅寫雜文〈喝茶〉,有云:「有好茶喝,會喝好茶,是一種『清福』。不過要享這『清福』,首先就須有工夫,其次是練習出來的特別的感覺。由這一極瑣屑的經驗,我想,假使是一個使用筋力的工人,在喉乾欲裂的時候,那麼,即使給他龍井芽茶,珠蘭窨片,恐怕他喝起來也未必覺得和熱水有什麼大區別罷。」顯系承襲此前所作〈文學和出汗〉,旨在宣傳文學的階級論;設若由此推測他自己那時仍然一點兒享喝茶「清福」的工夫都沒有,對照許廣平的記述,恐怕只能說是被魯迅的文章誤導了。
再舉一個例子。周作人說:「至於吃食,雖然在《朝花夕拾》的小引中曾這樣說:『我有一時,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:菱角、羅漢豆、茭白、香瓜。凡這些,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;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。』事實上卻並不如是,或者這有一時只是在南京的時候,看庚子、辛丑的有些詩可以知道,至少在東京那時總沒有這種跡象,他並不怎麼去搜求故鄉的東西來吃。」許廣平記述魯迅晚年生活,也說:「吃的東西雖隨便,但隔夜的菜是不大歡喜吃的,只有火腿他還愛吃,預備出來不一定一餐用完,那麼連用幾次也可以。素的菜蔬他是不大吃的,魚也懶得吃,因為細骨頭多,時間不經濟,也覺得把時間用在這種地方是可惜的。」
周作人提到「魯迅的照相大多數由於攝影時的矜持,顯得緊張一點」,我想起陳丹青說過,看了魯迅的照片,「以為魯迅先生長得真好看」,──魯迅的確「上相」,尤其是在那幾張流傳最廣的照片上,看上去特別乾淨瀟灑。當年有個十五歲的女孩馬玨親眼見過魯迅,所說卻大相徑庭:「一個瘦瘦的人,臉也不漂亮,不是分頭,也不是平頭」,「穿了一件灰青長衫,一雙破皮鞋,又老又呆板」;她大為感慨:「魯迅先生我倒想不到是這麼一個不愛收拾的人!」許廣平在女師大上課,對魯迅的第一印象是:「突然,一個黑影子投進教室來了。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約有兩寸長的頭髮,粗而且硬,筆挺的豎立著,真當得『怒髮衝冠』的一個『衝』字。一向以為這句話有點誇大,看到了這,也就恍然大悟了。褪色的暗綠夾袍,褐色的黑馬褂,差不多打成一片。手彎上、衣身上的許多補釘,則炫著異樣的新鮮色彩,好似特製的花紋。皮鞋的四周也滿是補釘。人又鶻落,常從講壇跳上跳下,因此兩膝蓋的大補釘,也掩蓋不住了。一句話說完:一團的黑。
那補釘呢,就是黑夜的星星,特別熠耀人眼。小姐們嘩笑了!『怪物,有似出喪時那乞丐的頭兒。』也許有人這麼想。」她概括說:「『囚首垢面而談詩書』,這是古人的一句成語,拿來轉贈給魯迅先生,是很恰當的。」
偶有例外。1931年8月17日,魯迅「請內山嘉吉君教學生木刻術,為作翻譯」,內山嘉吉記云:「片刻間,店門口閃了一道光亮,穿上一身雪白的長衫的魯迅先生走了進來。我不知道該怎樣描寫當時的情景,魯迅先生的服裝和外面的陽光正爭相輝映著。他那件長衫簡直像是用水晶織成的一般燦爛奪目。平時總見魯迅先生穿的那件是褪了色的似赭非赭、似黑非黑色的長衫,今天簡直使我大為吃驚。」嘉吉的哥哥是內山完造,「在講習班第一天結束歸來的那天,家兄也和我談起那件長衫,他也不禁『呵!』的一聲發出感嘆。」這倒適與陳丹青的讚美遙相呼應了。
回憶魯迅的文章很多,其中不少述及他的日常生活,又以許廣平和周作人所寫最為詳盡,可以抵得上《論語》裡的〈鄉黨篇〉了。周氏兄弟在東京時同居一室,據周作人介紹,魯迅每晚在洋油燈下讀書,「要到什麼時候睡覺,別人不大曉得,因為大抵都先睡了,到了明天早晨,房東來拿洋燈,整理炭盆,只見盆裡插滿了菸蒂頭,像是一個大馬蜂窠,就這上面估計起來,也約略可以想見那夜是相當的深了。」這裡提到魯迅幾樣生活習慣──菸癮很大,熬夜,再加上起床很遲,在他實乃至死不渝。許廣平說魯迅吸菸「每天總在五十支左右」;孔另境說他「菸是一支接著一支地吸,我幾乎從沒有見他的手指裡間斷過菸捲,菸的質地又是十分惡劣」。
魯迅還愛喝酒,郁達夫說:「他對於菸酒等刺激品,一向是不十分講究的;對於酒,也是同菸一樣。」孔另境所言略有出入:「每次吃飯都是要飲一些酒的,不一定飲多,但確為他所嗜愛,不過酒的質地卻異常講究,有一次見許女士親自為他用玫瑰花浸著什麼酒,有一次在他家吃飯,我飲了他幾杯紹酒,那酒味的醇厚,是我在上海任何朋友家裡都沒有飲到過的。」許廣平則說,魯迅通常「飲到差不多的時候,他自己就緊縮起來,無論如何勸進是無效的」。魯迅又愛吃零食,李霽野說:「先生是愛吃糖食和小花生的,也常常用這些來款客;有一回隨吃隨添了多次,他的談興還正濃,我料想兩種所存的不多,便笑著說,吃完就走,他說,好的,便隨手拿出一個沒有打開的大糖盒。這以後,有一回打開盛花生的鐵盒時,裡面適逢空無所有,他笑著說,這次只好權演一回空城計了。」許廣平則說:「糖也喜歡吃,但是總愛買三四角錢一磅的廉價品。」
總的來講,魯迅終生過著一種近乎波西米亞人的生活,而且辛苦忙碌,如俗話所云「蠟燭兩頭燒」。但有一點值得一提,即如郁達夫所說:「一般和我們在同時做文字工作的人,在我所認識的中間,大抵十個有九個都是把書齋弄得亂雜無章的。而魯迅的書齋,卻在無論什麼時候,都整理得必清必楚。」
孫伏園說:「他雖然作官十幾年,教書十幾年,對於一般人往往無法避免的無聊遊戲,如賭博,如舊戲,如妓院,他從未沾染絲毫。」許壽裳則說:「魯迅極少遊覽。」魯迅晚年愛看電影,如許廣平說「算是唯一的娛樂了」,而且每次的座位都是票價最貴的。「他的意思是,看電影是要高高興興,不是去尋不痛快的,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遠角落裡,倒不如不去了。所以我們多是坐在樓上的第一排,除非人滿了,是很少坐到別處去的。」去看電影,也不坐電車和黃包車,要坐小汽車。「晚間,小孩子睡靜了,客人也沒有,工作也比較放得下的時候,像突擊一下似的,叫一輛車子,我們就會很快地溜到影院坐下來。」魯迅平生所看的最後一部電影是《復仇豔遇》,時為1936年10月10日,去世前九天。他在日記裡評曰「甚佳」,胡風「後來聽見夫人景宋女士說,看了那以後的先生是高興得好像吃到了稱心的糖果的小孩子一樣」。魯迅還給朋友寫信,鼓動「不可不看」。該片原名《杜布羅夫斯基》,拍攝於1935年,改編自普希金的小說,片長七十五分鐘。這部電影如今只因魯迅才被人們提及,導演亞.維.伊萬諾夫斯基亦已隱沒不彰,他與魯迅同歲,多活了三十二年。
魯迅去世不久,周作人說:「一個人的平淡無奇的事實本是傳記中的最好材料,但惟一的條件是要大家把他當作『人』去看,不是當作『神』,──即是偶像或傀儡,這才有點用處。」二十年後,他又將此文收入所著新書,「神」雖改為「超人」,其實還是這個意思。
◎作者簡介
止庵
本名王進文,1959年生於北京,1982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口腔系(現北京大學口腔學院)。做過醫生、記者,曾任新星出版社副總編輯,現為自由撰稿人。出版有《周作人傳》、《樗下讀莊》、《老子演義》、《神奇的現實》等,並校訂《周作人自編集》、《張愛玲全集》等。
※延伸閱讀:
‧魯迅的成就
【完整內容請見《聯合文學》四月號318期;訂閱聯合文學電子版】
|